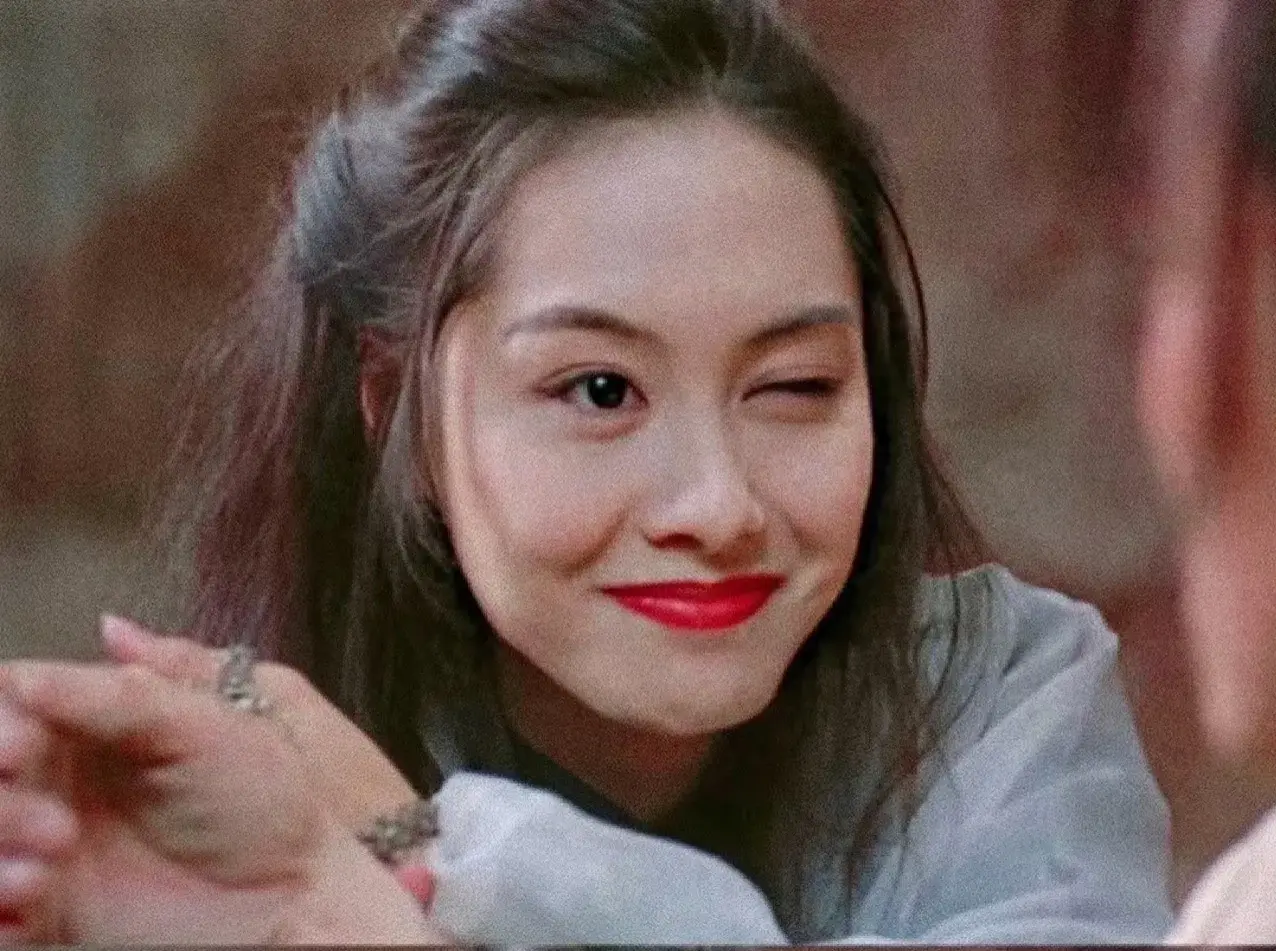我们和图像并行存在?在《人声》中:人类的终结,后人类的起始
谈到佩德罗·阿莫多瓦(Pedro Almodóvar)的《人声》时,我们不得不也看向在冰岛作曲家约翰.约翰森(Jóhann Jóhannsson)第一部、同时是最后一部导演作品《后人类传说》里,同样担任「女主角」的蒂妲·史云顿(Tilda Swinton)。


前者的蒂妲,源于改编自尚·考克多(Jean Cocteau)同名剧作《人声》中一位即将与恋人分离,而走向心碎与精神崩溃边缘的年轻女子;后者的蒂妲则是来自二十亿年后的人类,穿越至当代,向今日的人类发出警告,同时带来预言。
由上可知,蒂妲于两部电影中所扮演的角色,各自建立的视觉与叙事风格,毫无疑问是大相径庭的。
《人声》继承了阿莫多瓦创作脉络里一如往常的鲜艳配色,《后人类传说》全片唯一出现的色彩则是象征着「后」人类的「绿光」,也就是蒂妲所标识的绿色光点。不过,诡异的是,阿莫多瓦和约翰森似乎分别在两部电影里,表述了自身对于「人类」和「图像」的相似观点。

人类是美好的,由恒星孕育,亦由恒星毁灭。(Humankind is a fair spirit whom a star conceived and a star kills.)
《后人类传说》的结尾,蒂妲的声音再度出现,仿佛她并非以自己身为人类的角度来叙述这个她所认为的人类特质。如果象征蒂妲──意味着二十亿年后的「后」人类的绿光并非「人类」,那么此绿光的存在意味着什么?
反观《人声》的蒂妲,从最初买来一把斧头,不断挥砍着即将分手的「恋人」承诺要来领取的西装服,对着属于「恋人」的狗喃喃低语,最终将家中所有的物品、剧场/摄影棚般的布置浇上汽油,点火焚烧时,她仍在通话中对着那个我们始终没有看见人影、没有听见任何声音的「恋人」说话,并要求他「看向」他们曾经共创回忆的住处。

一瞬间,我们或许期望阿莫多瓦给予这个神秘的「声音」一些镜头,哪怕只是一个大远景,一个完全没有露脸的背影也好,但是我们最终仍什么也没看见。如同《后人类传说》的「人类」,以绿光的形式出现,最终也以绿光的形式归于黑暗,其余所见尽是工整对称、毫无生命力的建筑物。
或许我们曾经希冀这个随着说话频率变动的绿光,仅是一种信号、一种符号,象征着蒂妲、象征着二十亿年后的仅存人类,而并非「真正的」「人类」。

可随着时间的消逝,我们被迫相信银幕上的绿点即是仅存的「人类」:不会再有其他我们熟悉的、或是想像中的人类面孔出现,而蒂妲点火燃烧所有的家具与物品后,她将耳机随手丢在火场里,带着她与那位不可见的恋人曾经一同抚养的狗,离开陷入火海中的家,并对着它说道:「从现在开始,你必须习惯和我一起哀悼他,好吗?」
直至此处,如同我们于《后人类传说》落空、未能获得满足的期望,它再现于《人声》之中:那个没有面孔、没有声音、没有身形的「恋人」,他究竟以什么样的型态存在?。

此处,我们或许也能够合理怀疑,蒂妲与之通话的耳机,实际上并非传递声音的媒介,或是允许蒂妲得以通话的工具,而是蒂妲对话的唯一对象──也就是,耳机即是恋人本身,或这个「声音」即是恋人本身,也或者蒂妲先前发泄怒气的那套西服代替了恋人的现身。
毕竟蒂妲出于绝望而服下药物后,蜷缩依偎着那套仅存的来自恋人的东西:他没有形体、没有面孔,如同绿光一般,其本质即是一团不断晃动、不稳定的光。

于是,「后人类」传说,实际上意味着「没有人类」──至少没有我们认知里的人类。「人」声同样如此:没有人类,仅剩下声音。人类的形式以可视化的方式,被重新理解与体验,无疑对于仍身为认知中「人类」的我们,是为一种冲击与震撼:
不上不下、不里不外的悬置感(suspension)带来了不确定性,因为它不会让一个状态完全成形或产生明确的结论。

当我们重新以「绿光」或「声音」来理解人类时,不仅是我们对人类的认知于此终结,「我们」也于此时此刻终结。
「心灵的沟通已经不再有效,于是人类之间的沟通回到了语言符号系统。」这是身为绿光的蒂妲向当代人类发出的箴言之一。
身为少数、甚至唯一以语言及符号互相沟通及理解的生物,我们的生活以自身为中心,也因此鲜少注意到仅有人类仍以语言及符号交换信息的事实。

的确,身为后人类的蒂妲,也以绿光的频率及声音,向我们发出信号,而与「恋人」通话的蒂妲,则始终以声音传递自身的情感与情绪予看不见的通话者;可这句话的前半段──「心灵的沟通已经不再有效」──究竟指涉了什么事实?
首先,我们必须处理人类已经在这两部电影中以全新的形式,被重新理解的事实。
「心灵的沟通已经不再有效」,意味着我们──我们人类──于将来的二十亿年之间,发展了透过心灵沟通的能力。

就当前普遍的人类经验,多数人仍旧无法以心灵进行沟通,而「后人类」的蒂妲则表示二十亿年后,人类「不再」能够以心灵沟通,因此由此推测。现在到未来的二十亿年间,或许会发展出一种仅凭意识或心灵即可彼此交流的方式。
因此,若我们把《人声》视为我们所面临的「当前」──不论是考克多的写于1930年的戏剧,或是阿莫多瓦2020年摄于疫情期间的图像,《后人类传说》则视为久远、遥不可知的「将来」,我们便能将两部电影分别与「人类无法以心灵沟通」的两个时期有所对应。
如同前述所说,《人声》的蒂妲以语言传达情感,以片头及片尾的工具弯曲成斗大的字幕,《后人类传说》的蒂妲同样以图像──某种程度能够承载符号的系统与媒介──或声音向人类/观者发布预言。
《人声》—《后人类传说》之间的地带,或许正是那段我们尚未经历,也不清楚是否会经历的「去语言」/「去符号化」(desemiotization)的时代。

存在着「我们之中」的符号,这意味着可见形式在说话,而文字则拥有可见的现实重量,也意味着符号与形式交互散发出它们的感性呈现与意指之力量。
毫无疑问地,哲学家洪席耶(Jacques Rancière)的这段话指出了符号与可见/可视化之物之间的密不可分。
这也意味着,符号仰赖可视化的形象──如影像──来显现自身。而语言作为一种符号,我们仰赖符号将我们自身定位于世界中的相对应位置。
就《人声》而言,我们始终没能看见蒂妲通话的对象,他的声音及图像也无以企及,而《后人类传说》则是一个告诉我们他/她是「人类」,却不曾向我们揭示他/她的面貌的存在。
「人类」一词,已然分别在两部电影里,造成语言系统的能指(signifier)与所指(signified)关系崩解,图像上头亦然──毕竟「人类」在语言或图像系统之中,已经不再指涉我们所熟知的意义或形象。

于是,若我们假设《人声》与《后人类传说》之间,存在着一个去语言,也去符号的时代,一个人类仅透过心灵交流的时代,一个属于「完全人类」的时代,那我们或许也可以假设,这个时代也是图像的终结。
当我们的意识与视界里所想、所见的一切,不再需要透过媒介传递,图像必定也因此不再被需要,因为不再有任何事物是不能被意识所直接理解的。
至此,若我们将这样的转变对应至前述所说之「对人类的重新理解」,也就是以绿光或是纯粹的声音理解人类的存在──,我们同样可以将符号和语言系统的消失,让人类转以心灵沟通的过程,理解为一种生物学上的变态(metamorphosis)。
总结而言,《人声》与《后人类传说》皆各自以蒂妲这个不稳定的形象,来预示即将到来、也可能即将结束的图像终止时代,或是当今正在进行的人类意义终结的时代。

不过,这并不表示我们必须认为,这两部电影对于图像或人类的宿命抱有悲观的想法。
拥有了图像,我们便必须拥有语言与符号;反之拥有人类,符号与图像或许将被我们所抛弃,因此图像与人类似乎是无法并行存在的,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择,基于图像若不被视为视觉艺术,则其仅能是对于真实事物的复制与再现,永远不会是事物本身,永远仅会是象征某物的「符号」。
但是,《人声》与《后人类传说》中的人类已经崩解,两部电影所展示的人类,虽然仍透过媒介向我们显现自身,可他们的存在已经解构了符号系统。
失去形体、破坏符号、成为了光或声音的「人类」,间接暗示了在不远的将来里,我们或许便能真正地与心灵沟通──因为此刻,我们将成为如图像般的存在,成为一种传递的媒介,成为了承载思想的媒介与符号本身。

这同时意味着我们不必在人类的终结与图像的终结之间做出选择:图像不会带走我们的灵光,而我们与图像是可能并行存在的。
谢谢观赏,关注我,了解更多精彩。
欧阳娜娜直言自己害怕上热搜,不想上热搜的明星还有谁?
尽管普通人都羡慕明星身上的各种光环与巨大的经济价值,其实圈外人看到的往往都只是表象罢了,不到20岁的欧阳娜娜尽管靠强大的音乐技能加入了娱乐圈,但圈中的是是非非还是让她非常害怕的。在最新一期《我和我的经纪人》当中欧阳娜娜面对镜头表示“自己真的不是学霸”,面对上涨的热度与粉丝,娜娜经常不知道到底应该如何应对,她表示前一阵子登上热搜以后非常害怕,因为她认为只要登上热搜就会很容易被骂。娱乐天地2023-06-05 09:04:280000曝光!瞒了观众十几年,草根歌手王二妮真实身份被揭穿,真虚伪
在娱乐圈,有些故事从表面看起来平凡普通,但背后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,就如同一部扣人心弦的悬疑小说。草根歌手王二妮的身份揭秘,就是这样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。她那澄澈动人的嗓音,那仿佛天使的形象,都在瞬间崩塌,揭开了一个震惊众多歌迷的真相。娱乐天地2023-09-28 13:41:580000这张火遍全网的照片,背后的人“塌房”了
2015年,曾有一张“裙子到底是黑蓝还是白金”的图片火遍中国网络。据网友查证,这个讨论最先出现在英国的一个网帖中,当时网帖作者将这条裙子放置在不同光线下,裙子呈现出差异极大的两种质感,争论很快吸引了英国乃至全球的网友参与讨论。可就在近日,这位作者却被媒体揭露有严重的家暴行为,并因被指控杀害妻子未遂的罪名出庭受审。娱乐天地2023-07-18 14:39:050000著名演员梁天:不参加妹妹婚礼,大哥去世后看清英达,愧对宋丹丹
文|尼尔编辑|尼尔“你这不是当小三吗!你不要脸我们梁家人不要脸了?从今往后我就当没你这个妹妹!”喜剧演员梁天很少有这么动怒的时刻,他一生好脾气,没想到发过最大的一次火,竟是冲着自己的妹妹梁欢。但令人意外的是,梁欢却对哥哥的怒火无动于衷,而且她在看到哥哥的反应后,最后一丝顾虑也在这一时刻烟消云散。依旧一意孤行地要和英达结婚,还说道:哪怕最后落得个六亲不认的下场,也无所谓。娱乐天地2023-10-25 20:06:130000“天生苦相”的9位女明星,个个愁容满面,个个星途坎坷,真玄学
文|艺齐影纪编辑|艺齐影纪盘点这几位苦瓜脸女星,每一位女明星都气质出众,明艳动人,但都是星途多舛。这些和自己的付出和努力还有机遇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,但女明星的长相也非常重要。有趣的是对于一些靠长相吃饭的明星来说,其长相是毋庸置疑的出类拔萃,但就是没有观众缘。在娱乐圈,颜值即正义这句话被放大到极致。小编盘点了“天生苦相”的9位女明星,个个面露苦相,个个星途坎坷,真玄学。娱乐天地2023-07-27 20:48:1100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