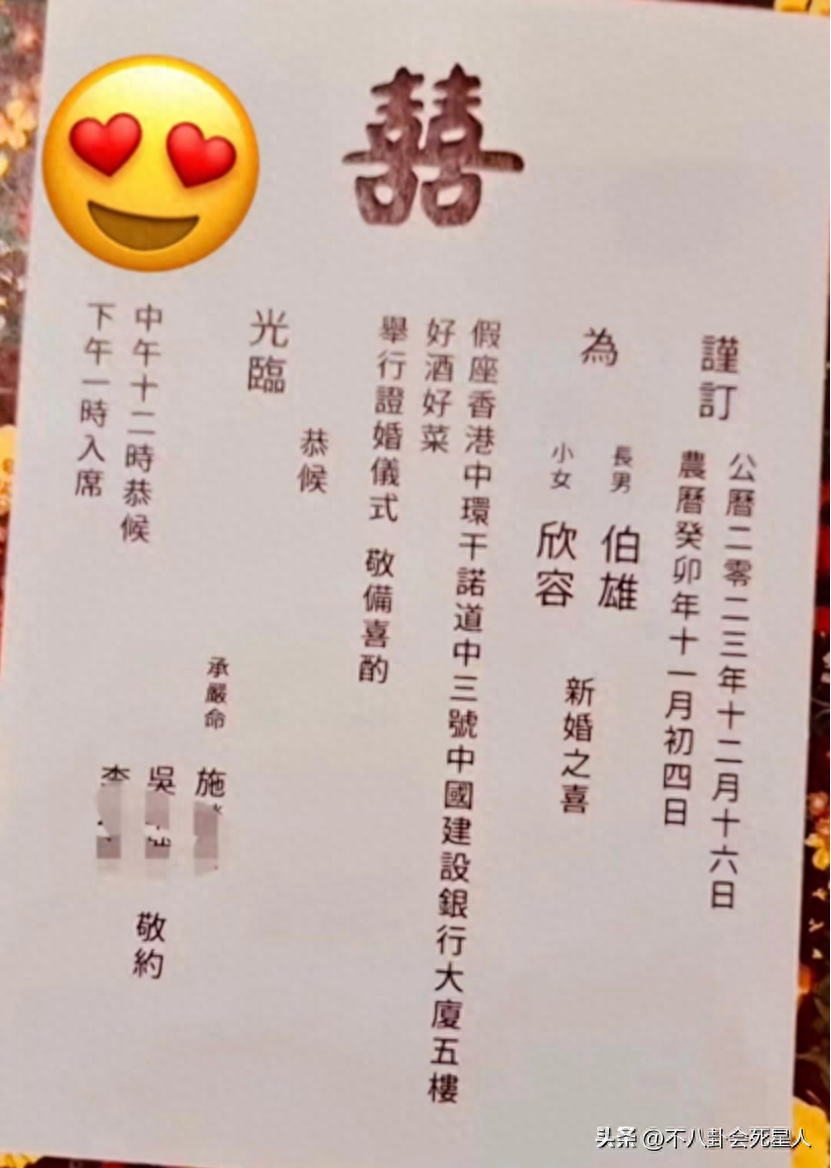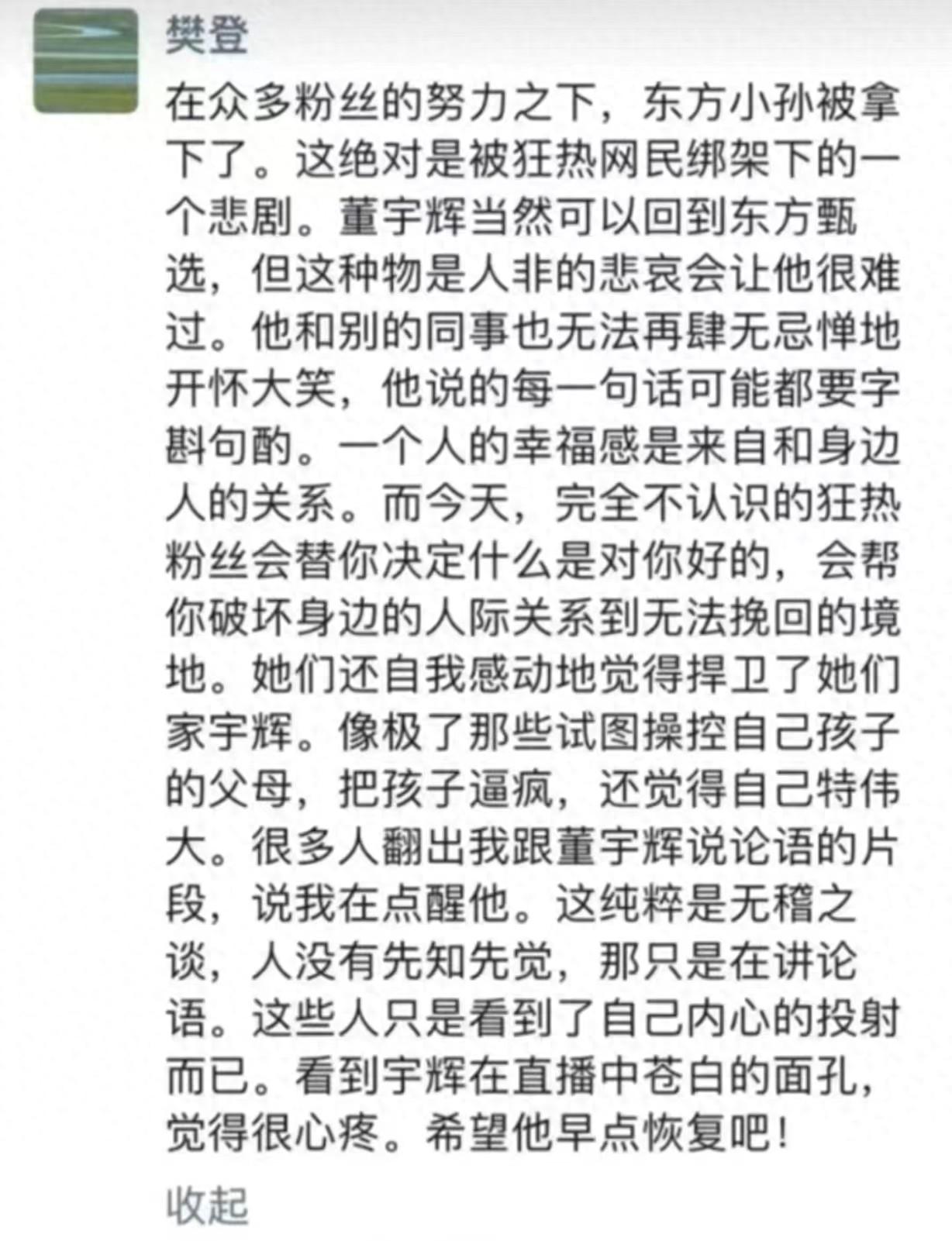镜像追问:镜像式影片的哲学沉思

电影作为一种具备直观表达性特点的艺术形式,通过描绘各种动人心弦的故事,给予观者特殊的精神关怀。
其中,有关镜像哲学电影的人文关怀大多体现在人类自我追寻的过程中,《情书》亦是如此。

在温暖悲情的情感基调下,《情书》撰写了现实个体自我追寻与救赎的寓言,透过大屏幕讲述了令人深思的哲学思辨和人性力量。
随着时代一步步的发展,人类的文化不断演进,心灵思想的艺术表达形式也在相应的变化。

巴拉兹在《电影美学》论述到:从古老的视觉艺术黄金时代伊始,艺术家通过绘画、雕刻等抽象的形式表现人的心灵。
自印刷术出现与发展后,人的心灵思想交流逐步集中于文字,开始减少使用身体器官这一表现工具。长期的文字传播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人们观看的眼睛,此时思维在抽象运动,利用形象表达的观念逐步减少。

此后,电影的出现在文化传播领域开辟了一个崭新方向,观众通过视觉来体验影片中的情感、情绪甚至思想。这种艺术形式不是代替说话的符号,而是一种直接可见的表达心灵思想的语言。
这些存在于视觉分析中的潜能力,能够将观者代入弄清那些潜在的本质。依照巴拉兹的观点,电影的影像叙事得以传播,使人们重新睁开“发现的眼睛”。

影像语言同文字语言一样可以给人以感性的审美感受,更蕴含了事物的特征与本质。如若能够用精神分析的视角去看电影,电影影像给予观者的感受,或许比生活还多。
欣赏电影,实际是暗渡情绪的一种方式,同时渗透着内心的欲望。心理学家施琪嘉在《观影疗心》里讲,对于长期生活在黑暗中的原始人类而言,光象征着天亮、希望和奇迹,而黑暗则象征着无望。

现实中,人们总将希望寄托于幻想,希冀奇迹的发生,因此沉溺于电影的虚幻之中。
对此,拉康利用精神分析学的知识对此种现象进行了深度的探讨分析。镜像理论作为一种分析电影的理论同样可以作用于现实。它诠释了电影具有深刻代入感的原因,分析了为何观众能够融入至眼前的荧幕中。

现实生活电影通过大屏幕的演示确立中心位置,电影体验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占据主体位置。此时,台下的观众聚焦于影片叙事中,已然被剥夺其主体存在的权利。在《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》中,齐泽克认为:“主体是大他者的空无,是一个空洞。”而拉康对此做出了补充,认为主体的出现是被动的,而一切都来源于他者欲望的需要。
欲望的空洞不断被填补,随之产生新的他者之欲望。由此观之,在拉康的理论视域中,想象和象征域的存在,都是在填补现实的空洞,正是空洞的显现才使主体现身于欲望。

因此,不能说意识形态生产了主体,相反,通过意识形态的运作去掩盖大他者的空无,而主体用一个幻想的内容去填补了空无。
观看电影的观众虽然经历了主体的暂时性缺失,但却从现实缺失中挖掘出了想象中的“自我”,这个幻象即为观影时的替代主体。
正如齐泽克所说,通过想象一个幻想的内容去填补真实世界中的空无,这是一种欲望的暂时性满足。

可以说,看电影即是一个想象代入的过程。观众融入影片叙事之时,便是融入了他人的故事,这一举动可称为是对自我的精神分析。
拉康认为,所谓精神分析,便是通过孤立出某个意义的失败点从而发现深层含义。正如电影的叙事表达,实则为一种被压抑的潜意识的裸露。

观者发掘潜意识的同时,便开启了一场精神上的自我分析。在《情书》中,那个总是被自己记忆所遗忘的角色便是藤井树(女),她好像总是忘却的,但在回忆中对一切却又是无限憧憬。
原本好似已经彻底遗忘了那个青涩少年,却在一封偶然的信件到来后,尝试打开被封存的心扉。

这时懵懂的藤井树(女)还是介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。在后来与博子的一次次对话中,无意地倾吐着自我本心,那是潜意识中自己看不到的另一半真实的自己。
电影在人的实际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,就是《情书》中的藤井树(女)。
藤井树(女)在电影中展示了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的真实轨迹,观看者也通过电影故事的书写和画面呈现,与真正生活中的自己达成某种和解。

海德格尔在其著作《存在与时间》中认为,人存在的本真为“求真”,但是人只活一次,一切都没有被改写的可能。
每每在经历选择、付出、失落过后,不免常常去幻想另一种可能,而电影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。

《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》在探求着不同维度下同一双生的多重命运。《情书》讲述着同一维度下多人在追逐回忆中重生。
他们都是经历过爱情、离别、生死后,仍然对生活保持着热爱与渴望,愿意以平淡的内心面对痛苦,接受生活的本质。

在岩井俊二的《情书》中,开场一幕已极具美感。博子在雪中漫步,没有台词的帮衬,单纯的将人物在雪景中的一举一动,通过远景与特写,描绘出博子的悲伤和思念——那是一种无声的祭奠与道别。
开场一幕刻画了以简为美的东方审美,展现了东方美学的精髓——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。画面植入观众的潜意识,没有过多的修饰和渲染,观者已然感知到博子的一切情绪,实现共情。

其次,影片中打动人心的便是青春年少之恋。岩井俊二拍摄的青春爱情,并不是俗套的告白相恋,而是心底的悸动,难以出口的羞涩和欲言又止的含蓄。含蓄,也是东方美学的精髓之一。
那是年少时期,少女树看着少年树,少年树一本又一本的借阅图书,在借阅卡上悄然写下她的名字时羞涩的笑容。
二人不曾对视,却早已互生情愫。寂静无声的教室里,只有沙沙的翻书声,映射着含蓄的情动时刻。

除了诠释含蓄的情动之外,《情书》同样呈现了对死亡的深刻探讨。藤井树(男)的死亡,使博子沉浸于悲痛中,更勾起了博子及家人伤感回忆。
在与藤井树(女)对话的开始,博子有意地隐瞒了藤井树(男)去世的真相。她说:“死亡是件可怕的事实。”藤井树(女)也同样面临死亡带来的伤痛。她无法释怀父亲的离世,陷入不自知的哀伤中。
这种不自知让她数次遭受感冒的困扰,在一次发烧中,得到了濒死体验,并出现了记忆深处的幻觉。

那是父亲去世后的又一个雪天,她看到一只被冰冻在冰层中的蜻蜓。这只蜻蜓唤起了她因父亲与藤井树(男)死去感受到的痛苦。
此时,与死亡和解,是生者必经的道路。那只冰冻的蜻蜓如同逝去的家人和爱人,他们并未消散,而是永眠于生者的记忆当中。
这一时刻,博子与藤井树(女)与死亡达成和解。“你好吗?我很好。”那是经历死亡后的重生,是抛却过去的新生,是自我的解脱与救赎。

片尾的“情书”,那份包含着三个人的情动回忆,最终在藤井树(女)身上永恒延续。爱而不淫,哀而不伤,这份情感延续着东方的温情,缓缓诉说。
《情书》用电影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的有关爱情的坚守、理解的善意故事,同样也是一则具有启发性的,释怀于生死之上的人生寓言。

多条双生叙事的人物塑造手法自始至终贯彻着人性复杂和矛盾,这种纠结情绪并非是“是”与“非”的较量,而是“执着”与“释怀”间的较量,表达着对陷于自我感动的人的同情与理解,和对生存与死亡的释然。
《情书》中没有对生死、爱情的思考套入一般结论清晰、先抑后扬的套路中,也没有将人类的自我追寻背后的思考完全集中在同一人物身上。

在过往人生的经验中,我们每个人都曾面临过“死亡”,这种死亡并非是真实的,而是象征意义上的,它是人与人之间继续联系、互相表达的不可逾越的障碍。障碍不单是生死,它随时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各个角落,或许是距离,或许是时间,而这都可成为现实存在的“死亡”障碍。
每当我们直面“死亡”时,无意识中就会选择去逃避,如同影片中的博子和藤井树(女)。

此时我们更希望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衡量、解释周遭的一切,这种对人性与人生的追问正是一种伦理诉求,其意义不仅在于社会的认可,也有益于自我对生命和生活的反思。
《情书》的电影理念展现的是本土文化的精华,影片所表现的隐忍爱情观源于东方文化,映射出日本电影乃至亚洲电影独特的东方风情。
亚洲电影中呈现的人文情怀,与西方所呈现的具有一定的差异,更注重表达对本土社会的针对性关注。

在东方美学的影响下,日本电影表达了对欲望与爱的深刻思考的同时,呈现出特有的东方温情。
此外,导演试图通过本片搭建人的情感世界与外在世界的联系,为人类自我存在与发展提供思考——如何通过外界镜像认识自己,通过他人眼光认识自己,通过自身感悟认识自己。
杨烁否认出轨聊天记录,揭秘杨烁与小2岁娇妻王黎雯的婚姻生活
近日,微博上挺热闹的,男星杨烁也上热搜了。而让人意外的是杨烁竟然被传疑似出轨了。网上传出了疑似杨烁与某美女的聊天记录。杨烁被传与某女子共度了一夜,并给了该女子1万块钱。杨烁疑似出轨的事情也引来了网友们的围观和热议。娱乐天地2023-06-05 05:55:16000030岁沈梦辰催杜海涛快点娶她,娱乐圈着急嫁人的女星还有谁?
近段时间以来,沈梦辰和杜海涛是凭借上综艺节目而人气大涨。沈梦辰看上去少女感十足,但她其实将近30岁了。近日,沈梦辰表示她最想被贴上杜海涛老婆的标签。许多网友评论说:沈梦辰如此大方示爱杜海涛,看来两人是真爱了。也有网友表示感觉沈梦辰这是在变相催婚呀!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娱乐圈着急嫁人的女星还有谁?你最喜欢谁呢?1、沈梦辰娱乐天地2023-06-05 13:46:050000奶茶妹妹衣品被无情吐槽!为何将上万元的衣服穿出地摊货的感觉?
7月15日晚,奶茶妹妹章泽天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组照片,奶茶妹妹身穿红色礼服裙,站在刘强东身边尽显窈窕身材,和加拿大总督握手,老板娘气质十足。网友们纷纷评论说:“真的是太有气质了,越来越喜欢这对夫妻同框了”、“奶茶妹妹的美真不是盖的,刘强东有福气啊”、“啊!奶茶妹妹太美了”!曾几何时,奶茶妹妹的衣品是被网友们无情吐槽的!好多网友都表示不解:奶茶妹妹为什么有本事将上万的大牌穿出地摊货的感觉??娱乐天地2023-05-26 02:06:010000琼瑶奶奶,墙都不扶,就服你
如果你看过琼瑶的生平简介,你一定会觉得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失去了色彩。当《情深深雨蒙蒙》里的主角说着:“你无情!你残酷!你无理取闹!”时,八十多岁的琼瑶则用一句:“这一生是我锁住了你,还是你锁住我”,让看客们拍案叫绝。实在无法想象,人至暮年,她的感情依旧充沛,如琼瑶所有的作品主题一样,她的眼中只有爱,山盟海誓、海枯石烂等经典桥段都是她生活的重现,她说人的一生没有真正爱过,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。娱乐天地2023-05-06 18:10:3100003.2万人预约的《清落》要来了!一集吻四次,刘学义还成了奶爸
10月过半,2020年仅剩2个月,年终将近,各大平台都推出了不容易出错的甜宠剧,像“猕猴桃”有《明月曾照江东寒》、《如意芳菲》,鹅有《今夕何夕》与《燕云台》,而酷在推出《将军家的小娘子》后,又会上线一部绝世甜剧—《清落》。娱乐天地2023-05-06 15:46:220000